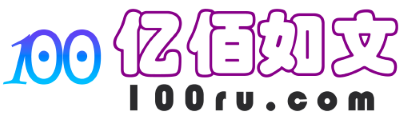
“印国。”
“对!印国买的!当时街上排长队啊,为那个老板请愿,我还记得那老板姓......”
“钟。”
“对!钟泰康!好名字啊!”
他似乎想起编织袋上的名字,扭头看向后座,整个人愣住。
我回复道:“那个老板就是我爸。”
被宋淮安亲手送进监狱,抗癌药走私案的被告。
顾宇听闻惊呼,又是一脚刹车:
“钟医生!原来你爸是药神啊!”
随即又将故事串起:“宋大律师,老丈人,爸?”
“所以,也就是说宋律师是你前夫,把你爸送进了监狱?”
曾经光是提起就痛得无法呼吸。
可如今我的心里再也掀不起波澜。
车内寂静无声,只有空调嗡嗡地吹着热气。
顾宇尴尬地挠头,想转移话题:
“袋子里是换洗的衣服吗?我帮你洗。”
我望向窗外的雪花,轻声说:
“不用了。他不需要了。”
一年前,父亲就去世了。
可我前几天才知道。
我检查出白血病,医院联系父亲骨髓配型。
我才得以肯定,父亲真的不再了,而不是为了见我一面的说辞。
他心脏病突发,据说走得安详。
给我留了厚厚一摞的信,每封都有:
“蓉蓉好好生活,不要怪爸爸,不要怪淮安。”
我从来没有怪过他。
我只是在怪自己。
怪十五岁那年给自己捡了个哥哥。
没有他,也许爸爸不会入狱,也不会死。"